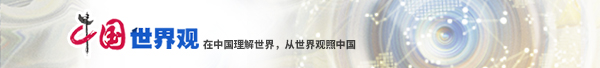“民間文化的拾荒者”:“撿拾”民藝,記住鄉(xiāng)愁
“一段日子不去趟村子就覺得不行,只要去村里,總能有交流有收獲。”潘魯生靠坐在國家博物館南1展廳外的長凳上,姿態(tài)隨意,如同下鄉(xiāng)調研時盤坐于老手藝人的炕頭。
南1展廳正在展出“記住鄉(xiāng)愁——山東民藝展”,1500余件(套)民藝展品都來自他多年下村中的“拾撿”,那些鍋碗瓢盆、桌椅板凳、被褥衣裳、農(nóng)具玩具……被拭去時間的塵埃,擺放在博物館里,琳瑯滿目地展示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的方方面面,帶著叫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氣息。
“辦公桌”早搬去了田野,這位有著中國文聯(lián)副主席、中國民協(xié)主席、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等多重身份的畫家和學者,常年在各地鄉(xiāng)村采風調研,他說民藝是鄉(xiāng)土中來的,要到田野里去傳承和發(fā)展,不能固守書齋和博物館。
研究民藝40年,潘魯生收集的民間生活器用及手工藝品已達萬余件,他帶著團隊調研過460個傳統(tǒng)村落,采訪了3000多位民間藝人,記錄民間藝術項目260項,留存文字資料1200余萬字,錄音資料5萬分鐘,圖片資料10余萬張,影像資料6萬分鐘……有媒體因而把他稱作“民間文化的拾荒者”。
從上世紀80年代起,潘魯生從鄉(xiāng)土民間先被熟視無睹,后在時代更迭、社會轉型中被輕易舍棄的老手藝和老物件里看到了美,認為其中有中國人的精神故鄉(xiāng),擔心“當人們認識到這種價值時,這些東西可能已經(jīng)沒了。”
他感嘆人們寄托鄉(xiāng)愁不能只有一輪明月,還有煙火生活,要留住鄉(xiāng)愁的載體和文脈。
看見民藝之美
“記住鄉(xiāng)愁——山東民藝展”7月中旬在國家博物館開展。很奇妙的,這個名字樸實、展品也樸實、還充滿地域色彩的展覽得到了來自天南海北的觀眾的喜愛。
國博工作人員介紹,暑假期間這個展尤其受孩子們青睞,展廳里總逗留著許多小朋友。
國博副館長劉萬鳴見過一位來參觀的母親指著油燈,跟孩子說你姥姥當年就用這個燈給你姨你舅你媽媽縫衣服,小孩聽了突然說了句“慈母手中線”。
還有人拍下一個籃子的照片發(fā)給朋友,說在展廳里看哭了,饑荒時,他跟奶奶討飯就用的這樣的籃子。
“多好看啊!”一口北京腔的女士從年畫到花布拍了無數(shù)張照片。她背后獨自前來參觀的大爺操著濃重鄉(xiāng)音興致盎然地念著展品名字,“這是茶壺套!”“這是蟈蟈葫蘆!”“這是魚盤!哈哈!”
“無論什么年齡、職業(yè),無論見過這些東西,還是沒見過,人們只要進入這樣一個空間,就會自然產(chǎn)生聯(lián)想和興趣,因為這里面有我們文化的記憶。”潘魯生說。
在展廳里走了一圈,他停留在一組人物題材的“孩兒模”前,“這是我小時候玩過的,20世紀80年代做民藝研究時,我回老家山東曹縣的老屋里找了出來。過去大人用磕子做面食,小孩用孩兒模和泥巴過娃娃家,這種模具題材多樣,有動植物、十二生肖、戲曲故事、民族英雄人物……是我們當年的百科全書,從中不僅能學到知識,也教給孩子怎么做人,不要走樣。”
“手藝是母親的藝術。”轉身看到旁邊展柜里各種兒童穿戴的圍兜、虎頭鞋帽、小衣服,潘魯生說:“生活中母親為孩子做的一切都是藝術,因為它教化孩子什么是美的,什么是善的。”
從小學畫畫,潘魯生曾在工藝美術公司做過一段時間設計員,耳濡目染,越來越喜歡民間藝術。
在大學,他開始學習和研究民間美術,不斷下鄉(xiāng)尋訪老手藝人,收集、記錄、整理和研究民間手工藝作品,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思考民間文化的價值。
改革開放后,西方現(xiàn)代派藝術涌入中國,形成熱潮,在帶來新氣象與新思考的同時,也引發(fā)對本土藝術的再認識。
當時,潘魯生被借調到北京,在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《中國美術史》當資料員。置身美術史的視野中,他有了個夢想——建一家民藝博物館,向社會免費開放,記錄和傳播中國傳統(tǒng)民間文化藝術。
在鄉(xiāng)野間真切感知到社會變遷,目睹傳統(tǒng)手藝的流失,也在研究與文化藝術交流中愈發(fā)深刻地感受到民藝的價值和意義,潘魯生覺得“我們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”。他篤信民藝之美,也希望更多人看見這種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美。
1998年,經(jīng)過十年籌備,潘魯生在山東正式注冊成立了的中國民藝博物館。本次國博“記住鄉(xiāng)愁”展覽的展品,就主要來自該館館藏。
讓民藝“活”在當下
1997年,潘魯生提出“民間文化生態(tài)保護”的命題,引起學界和社會各界關注。
他認為民間文化也是一種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,如同自然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一樣,民間文化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也在工業(yè)社會的發(fā)展中遭受破壞,而民藝處境嚴峻的根源正是其所依附的民間文化與民間生活的喪失。
在一篇呼吁保護民間文化生態(tài)的文章中,潘魯生寫道:“我們沒有理由不像保護生態(tài)平衡、保護珍稀動植物那樣保護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的手工文化,保護正在遺失的傳統(tǒng)。假如有一天我們身邊的傳統(tǒng)文化真的消亡了,我們會不會像忍受自然對人類的懲罰一樣忍受文化的枯竭,忍受文化生態(tài)的失衡呢?”
他將這篇十余年前的文章放在國博今年為“記住鄉(xiāng)愁——山東民藝展”出版的展覽圖錄序言位置,再次發(fā)出保護民間文化生態(tài)的呼吁,提醒人們?nèi)蚧瘯r代更需要提高文化自覺和自信,需要民族化、個性化,要重視民族文化和民間手藝,并使之“活”在當下。
幾十年來,潘魯生始終希望能讓更多人關心民藝,讓手藝的價值得到更廣泛的認同,他認為這需要把民間文化創(chuàng)新理念和現(xiàn)實生活結合起來,讓手藝重新回到人們的生產(chǎn)生活中。
“提出‘民間文化生態(tài)保護’后,我們做了‘手藝農(nóng)村——特色產(chǎn)業(yè)扶貧計劃’實踐項目,走了很多地方,也和農(nóng)民合作,參與民間手工藝產(chǎn)品的設計。我們發(fā)現(xiàn)手藝做好了,是能幫農(nóng)民脫貧致富的,民藝工作者應該把設計、創(chuàng)意和研究真正服務于老百姓。”潘魯生說。
近年來,作為全國政協(xié)委員,潘魯生多次建議在民族傳統(tǒng)工藝資源豐富的少數(shù)民族及貧困地區(qū),依托傳統(tǒng)手工藝開展精準扶貧,“鄉(xiāng)村振興”是他時常提及的高頻詞。
對話:民藝教給我們樸素之美
草地:您創(chuàng)辦的中國民藝博物館,現(xiàn)在觀眾多嗎?
潘魯生:多,它現(xiàn)在設在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博物館,在大學城里面,很多中小學生都會去看,我們的老師上課時也會帶學生去看家具、服飾等實物,可以說已經(jīng)成為一個課堂。我覺得這種教育價值比單純的公共展示價值更高,可以提升年輕人的文化認知和審美。
最早做這個博物館時,我就想著讓孩子們都來看看,懷著這樣簡單的愿望,到現(xiàn)在我也還是這么一個愿望。
草地:您提出的“民間文化生態(tài)保護”引起過很大反響,現(xiàn)在20多年過去了,在您看來,我們今天的民間文化生態(tài)有什么變化?
潘魯生:20世紀90年代我提出“民間文化生態(tài)保護”,是因為感到保護民間文化不能局限于單獨保護一個一個物件,民間文化是個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,它是傳統(tǒng)手工文化的生存環(huán)境,需要整體去保護、傳承、創(chuàng)新和衍生。這種保護是保護我們文化的基因和種子,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。
比起20年前,現(xiàn)在情況好了很多,大家逐步認識到民間文化的價值,傳統(tǒng)手工藝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(chǎn)受到重視和保護。如果我們這次的展覽是在20年前辦的,也許不會有現(xiàn)在這么多人來看。
草地:但提到非物質文化遺產(chǎn),還是挺容易聯(lián)想到冷清中艱難堅守這樣的形象。
潘魯生:“非物質文化遺產(chǎn)”是個引入的概念,由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,我們翻譯成這個詞。“遺產(chǎn)”聽上去是一種遺留物,其實我們更要保護活態(tài)的文化,它指向的不是物質形態(tài)的物件,而是無形的文化。從這個意義上看,我們不能只把傳統(tǒng)手藝作為“遺產(chǎn)”看待。
草地:您很在意一些詞的用法,過去也說過不主張對民間文化使用“開發(fā)”這樣的詞,而應當說“發(fā)展”。
潘魯生:對,“開發(fā)”,往往是抱著一種特定的目的去發(fā)掘和利用;“發(fā)展”,是尊重文化的本體。用詞的背后體現(xiàn)的是人的理念,我們要以合理的態(tài)度和理念對待文化。
草地:前兩年,日本漆藝師赤木明登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曾說:“中國欠缺的不是做好東西的人,而是用好東西的人。”做的人有,但沒培育出來使用的人。您怎么看?
潘魯生:我們要培養(yǎng)我們的審美,從民藝中,人們應該能看到中國樸素、美好的生活,而不是看到民間的、傳統(tǒng)的,就覺得土氣,覺得不夠高大上,不夠有品質。所謂的生活品質是一種內(nèi)在的質量,民藝教給人們樸素之美。我們需要加強美育,包括從娃娃抓起,從教育抓起,讓孩子從小認識和接觸手藝。(記者王京雪)